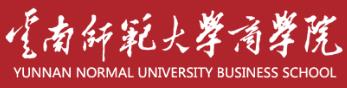薄伽丘与《十日谈》
2011/4/1 22:17:00 114招生网天津站 【大 中 小】
1348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肆虐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人口锐减。当时的欧洲人把这瘟疫称为“黑死病”(实为鼠疫),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教会借机要人们忏悔、祷告,用禁欲主义的说教攻击人文主义者个性解放的要求,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次逆流。恰在此时,薄伽丘的《十日谈》问世了,它以对现实幸福的大胆追求,给禁欲主义神学以迎头痛击,受到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和彼特拉克一样同属于意大利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商人,母亲是法国人。童年时期,薄伽丘就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性格,是个爱惹事生非的“孩子王”。成年后他拒绝父亲要他涉足商界的殷切希望,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和文学创作情有独钟。薄伽丘的学习过程也与别人不同,他不愿意完全按照刻板的师徒教学模式按部就班地掌握知识,而是按兴趣和需要大量阅读、钻研古代典籍,自学成才。他是意大利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学者,对拉丁文和当时流行的俗语也掌握得炉火纯青。在商贾云集、世风开放的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地,青年薄伽丘也曾一度放荡不羁,追求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直到父亲的商行破产,不久老父又撒手人寰,薄伽丘才如梦初醒,浪子回头,节衣缩食地赡养家人。后来的薄伽丘回忆早年的荒唐经历,常有不堪回首之感,但当我们看到《十日谈》中那一幅幅五光十色的风俗画,读到一则则散发着浓郁市民生活气息的故事时,却不能不感慨生活对作家的厚赐。才华过人的薄伽丘用俗语和拉丁语写了不少作品,又对古典文化颇有研究,这使他声望日增。1373年,他受聘在圣斯德望修院主持面向公众的但丁讲座,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
薄伽丘初登文坛时曾立志做个优秀的诗人,这是当时文学界的传统:轻散文重韵文。他曾在自传中说,自己独自研究赋诗法,尽力领悟诗歌艺术的真谛。他也确曾创作过不少爱情题材的抒情诗和叙事长诗,这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诗《菲洛斯特拉托》和《菲爱索莱的仙女》。但比起他的挚友、诗人彼特拉克那清新、流丽的诗歌,薄伽丘自愧弗如,于是专心致力于散文体的小说创作。要说讲故事,薄伽丘的确是个行家里手,青年时期写成的中篇小说《菲亚美达》,就把自己对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的女儿玛丽娅的爱情演绎得委婉动人,甚得时人好评。
薄伽丘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于1349—1351年间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这部文艺复兴早期产生的名著,为作家赢得了“欧洲短篇小说之父”的不朽声名。小说的时间背景就是欧洲大瘟疫时期,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丧钟乱鸣,一派恐怖景象。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为避难躲到效外的一座别墅中。此外宛如世外桃园,但见春光明媚,流水淙淙,花团锦簇,鸟鸣啁啾。欢乐总与青春相伴,惊悸之情甫定,十位贵族青年便约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光,用笑声将死神的阴影远远抛诸脑后。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恰好有了一百个故事,这是《十日谈》书名的由来。
翻看《十日谈》,就仿佛在欣赏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市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尽管小说的素材不仅仅来源于意大利的城镇社会,连中世纪的传说乃至东方文学中的某些故事都成为薄伽丘编织故事的素材凭据,但所有的故事却都是讲张意大利市民阶级听的,从内容到叙述形式都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故事中的人物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行各业人士:从封建贵族中的国王、王子、贵妇人到宗教界的神父、修女、修士;从学者、诗人、艺术家、穷学生到银行家、旅店老板、船主、面包师、手艺匠;从农夫、奴仆、朝圣香客到高利贷者、守财奴;从酒鬼赌徒、海盗、无赖到流浪汉、落魄战士、招摇撞骗的食客,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搬演了一幕幕或喜或悲、妙趣横生的话剧。
小说的主旨在抨击禁欲主义,歌颂爱情,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在第四天的故事开头,作家自己出面讲了个“绿鹅”的故事,颇能表达薄伽丘的创作意图。一位父亲将儿子从小带至深山中隐修,以杜绝人欲横流的尘世生活的诱惑。儿子到了18岁,随父亲下山到佛罗伦萨,迎面碰上一群健康、美丽的少女。头一次见到女性的小伙子问父亲这是些什么东西,父亲要他赶快低下头去,说这是些名叫“绿鹅”的“祸水”。 岂料一路上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儿子却偏偏爱上 “绿鹅”, 恳求父亲让他带一只回去喂养。 老头儿这时才明白,“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了”。
《十日谈》塑造了众多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薄伽丘看来,要想突破禁欲主义的束缚,首先就必须把受压迫最深的女性的天性解放出来。为此,作家在小说中公开自称是个天生的“多情种子、护花使者”,要为女性仗义执言。在第二天第十个故事里,一位精力旺盛的少妇把一个海盗当作自己的情人。当她年老体衰的法官丈夫斥责她不守妇道时,她为女性的天然权利据理力争,宁愿抛弃“觉得研究法律比了解女人的心理”更重要的丈夫,也不愿辜负自己的大好春光。第六天第七个故事讲到一个女人因奸情败露被丈夫告上法庭。按该城法律,与人通奸的妇人要处火刑。这妇人面对法官对罪行毫不推诿,但她同时提出,一条法律既应该适用一切人,也应该在制定时征得普遍的认可。可法律只惩戒妇女,立法时也不曾征得她们的同意,完全是不公正的。在这女人的质问下,法庭不但无法定她的罪,而且这条法律最后也被修改。在当时的男权世界和社会风氯中,偷情是男子的专利,女性则只能被禁闭在闺房中,充当男性的玩偶或过着无欲无爱的生活。 为了报复那些花花公子式的丈夫们, 作家甚至写了一组机智、勇敢的妻子如何愚弄自己的丈夫,与情人幽会的故事。平日趾高气扬的男人们不是钻进大酒桶里就是被关在门外,或是莫明其妙地被痛打一顿,甚至不明就里地为正与情人幽会的妻子在外守护,实在是蠢不可言。
《十日谈》中有许多正面歌颂青年男子冲破封建教条、追求爱情幸福的故事,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格调高雅、健康的。第四天“伊莎贝达的故事”,第五天“纪安尼的故事”,都写到少女反抗父母干涉,勇敢地也恋人相结合。 第四天第八个故事中,纪洛拉摩为情而死, 情人抚尸痛哭,心碎而死。第五天第九个故事中,写费得里哥为得到心上人的爱情而杀死心爱的猎鹰,这类故事写得情真意切优美动人。全书思想境界最高的当属"绮思梦达的故事"。郡主冲破封建门第观念,与仆人相恋,事情败露后,父亲暴跳如雷,将仆人关入地牢,痛骂她不顾身份,竟与下贱的奴仆相爱。 绮思梦达却宁死不屈, 并愤然驳斥父亲:“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样的机能,同样的效果同样的德性。我们人类向来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德性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
作家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赞美爱情,同情女性,就必然要抨击禁欲主义,揭露宗教人士的虚伪和神学教条对人的正常欲望的压抑,这是《十日谈》主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第三天第八个故事,一位修道院长愚弄一对农民夫妇,以满足自己的禽兽欲望。他将农夫关入地窖,让农夫误以为到了阴间,自己趁机去奸淫农夫的妻子。不料农夫之妻怀孕为掩盖丑行,修道院又将农夫放出,还无耻地宣称正是由于他的虔诚祷告,农夫才得以生还并喜得贵子。
第九天第二个故事里,有一位平日道貌岸然、严守寺规的女修道院长。一天她接到报告,一位修女竟与情人在修道院里幽会。大堂之上,院长气急败坏地痛骂不休。满面羞惭的小修女猛一抬头,却发现院长头上戴的不是头巾而是男人的短裤,院长顿时狼狈不堪,原来当别人向她报告之时,她正与男人鬼混,因起床匆忙,乱中出错,这才有了这戏剧性的一幕。薄伽丘对笔下的教会人士其实有所区分,对那些“犯戒”的小修女和小修士们他抱有同情,因为修道院的高墙毕竟无法阻断人的正常欲望。一位教士欲向一位妇女求欢,妇女指出他的身份与其要求不符。教士却回答说:“太太,我只要这件法衣一脱--这当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就成了一个普通的男人,而不是什么修道士了。”
但对那些利用宗教身份为幌子,专行男盗女娼之事的主教、院长、教士们,作家则毫不留情地予以辛辣的讽刺。一位神父竟给自己装上一对假“翅膀”,冒充天使长加百利,去诱奸教区内的一位农妇。这些自称“牧人”,要引导信徒灵魂追求天主之道的丑尖,其好色贪财的本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薄伽丘对男欢女爱的描写, 并不是无可挑剔的, 有些段落的文字显得低俗,甚至有色情之嫌。大概这个文坛上的“第奥纽”(小说中的人物)早已料到别人会对此有所诟病,氢预先就为自己做了精彩的辩护:“这些故事也跟天下任何事物一样,能够使人受害,也能够使人得益,这完全要看听故事的人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酒对于健康的人是无上妙品,可是对于发烧的病人,酒却是有害无益的东西,我们难道因为发烧的病人喝不得酒,就干抹杀酒的价值吗?”这听起来好象也有一番道理,但对人的情欲的“过度”的描写,甚至以不无欣赏的态度去渲染,毕竟不能否认其消极影响。
从根本上说,早期的人文主义中就有享乐主义因素,从当时留下的文献及后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意大利城镇生活的自由、开往程度也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对14世纪的薄伽丘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十日谈》的伟大意义更不能因此而被低估,历史的局限性毕竟是无法避免的。
《十日谈》以散文体的意大利通俗语写成,这不仅为意大利散文创作奠定的基础,也对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百个故事长短不一,最短的约千字左右,最长者则达一万五千字左右。从叙述的角度看,故事多采用作家所说的“平铺直叙”的方法,但在许多故事中,作家注意到了情节发展的转承转合,笔法简繁有度,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生动,语言个性化,富有喜剧性。因此,正是薄伽丘创立了欧洲文学史上短篇小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整部书的总体结构也颇具特色,它基本上以“天”为单位,根据故事内容的特点,把一百个故事按不同主题或类分开,每篇故事之前,都有讲故事人的一段开场白,引出故事。人们称《十日谈》的结构为“框形结构”,它被许多后来者所模仿,影响欧洲短篇小说集的构成型态达三百年之久。
《十日谈》以其对现世幸福的大胆追求和对禁欲主义的猛烈抨击,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也就必然遭到天主教会的极度仇视。教会公开谩骂《十日谈》是一部“淫邪之书”,社会上的各种反动保守势力也联合起来围攻作家,薄伽丘甚至遭到人身威胁,作家终于动摇了。
《十日谈》完成三年后,薄伽丘写了最后一部小说《大鸦》(1356),令人惊讶地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判逆思想,斥责女人是万恶之源,爱情是淫荡的肉欲。如果不是彼特拉克的劝阻,作家甚至打算将《十日谈》付之一炬。
1374年,彼特拉克病逝,薄伽丘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知音,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翌年便在病痛和贫困中辞世。教会仍然没有放过他,挖掉了他的坟墓,砸毁了他的墓碑。
版权所有 © 北京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天津114招生网 – 天津招生考试网,天津高考政策,天津高校推荐,天津自考成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胜古中路1号蓝宝商务大厦402 邮编:100029
电话:010-80788512 传真:010-80788512
ICP备案号:京ICP备12024748号 技术支持:中国网库[
31.25]